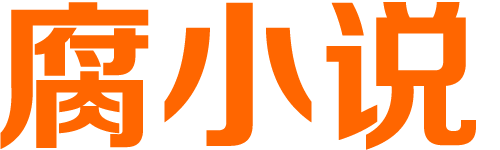吞雨(67)
谢桥睁开了眼,却也没看他,把手里那种画丢到他怀里,语气生冷,“你现在就走。”
纪真宜无暇去接,画轻飘飘落在地上,“突然怎么了?”
“我累了,没意思。”
谢桥看着他,漂亮幽邃的眼里灰冷一片,纪真宜几乎能感受到他那种破碎的无望,心尖都跟着颤起来,“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了?你告诉我好不好?我给你道歉。”
“你没错,是我活该。”谢桥嘴角扯了一下,很悲凉的自嘲,“你走吧,我看着你,觉得很烦。”
纪真宜心被他这句话剁成馅了,黑眼珠在眼框里仓皇无措地转动,他拽住谢桥运动服的上衣,嘴唇都哆嗦起来,“为什么?你说清楚,怎么突然就烦了?”
谢桥撇过身,“你不走我走。”他还没到那个地步,把自己的卑微和盘托出,他不想再把铮铮的骄傲让人寸寸折碎,变得可笑又可悲。
他就真转身要走。
纪真宜把他拖住,垂着头,嗓子里有些窒涩的哑,妥协地说,“你别走,我走,我走。”
早秋的夜大致还是热的,依稀有了点萧瑟的寒意,纪真宜伶仃地走在深夜的街头,肩头沉沉地塌着,路上几乎没有行人,只偶尔有辆车飞驰而过。
前几天他才跟他妈说“谁会把我赶出来”,今天就被赶出来了,果然话不能说得太满。他形单影只地站着,看着深夜的街道,一时间怅惘难消,觉得路灯的光都清冷冷的分外孤单。
身上什么都没带,还好有手机,没带身份证住不了酒店,正思忖着该在哪落脚,田心的电话就来了。
那边羞愤地质问干嘛让谢桥打电话,吓死他了,又问纪真宜真要转一线啊,噼里啪啦嘴上不停,看来确实消气了,“我递名片的时候都没想到谢桥真会存我电话呢,你俩这是在一起了?”
纪真宜顿住了,长呼一口气,“没有,我被赶出来了。”
纪真宜用老地方藏的钥匙打开了田心公寓的门,田心出差已经一周,屋子里很空。
他把自己抛到床上,却又睡不着,坐起身看电影,iPad没能拿出来,只好用手机,看《夺命五头鲨》。
其实他是不想跳过四看五的,奈何这个剧组好像已经智障到连数都不会数了,竟然没拍《夺命四头鲨》,只能将就着看五了。
鲁迅所有的书纪真宜基本都买了,当时没能全部搬走,留了许多在田心这。谢桥当年推荐他看鲁迅诚然是再正确不过了,鲁迅伴着他走过太多个好似等不来白昼的黑夜,他甚至觉得他要和鲁迅过一辈子了,当然鲁迅可能不太愿意。
他又开始翻,一页一页,从祥林嫂到刘和珍再到阿Q,从“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到“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再到自欺欺人的阿Q精神。
他活学活用——没关系的,以后他跟谢桥在一起了,一直生活下去,那跟寻常夫妻也没什么两样,谢桥就是他老婆,哪个男人没有被老婆冷过,骂过,赶出去过呢?
没什么的,纪真宜,你不会这点小事就哭吧?
眼泪啪嗒啪嗒往下砸。
他边啜泣边想,鲁迅写得真好,《夺命五头鲨》拍得真感人。
眼泪簌簌不止,他的脸又苍白起来,悲恸委屈的水红布满他整张脸,他抬起胳膊来揩了揩脸,眼睛里的水擦也擦不完。
他觉得自己真怂包,二十几岁了还因为这点小事哭哭啼啼,鲁迅见了都要说,“我们先前比你苦的多了,你算是什么东西?”(改自《阿Q正传》: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了,你算是什么东西?)
可是好难过,他说不清是谢桥说他不配,还是说看见他就烦,或是叫他走,哪一个更难过。明明就说了那么几句话,怎么个个字都往他心口扎呢,这些话换任何一个人说,他都觉得无所谓,甚至还能自嘲,可谢桥一说,他胸口就跟被人抡了一锤似的,每说一个字就陷下去一块,简直要体无完肤。
他跟自己说,谢桥当年也为你哭过,就当还给他了,没关系,今晚哭完,明天就去问清楚,别哭得不明不白。
纪真宜不喜欢的人他绝不拖泥带水,他喜欢的人见了棺材他也要扛走。
第二天他那条新闻三审完毕他就走了,在银行大厦没等到人,又回了谢桥的房子,按了很久的门铃也没人看,他蹲在门口等着谢桥回来。
门其实是指纹锁,但纪真宜不敢开,他怕看到他的指纹已经被清除了,也怕谢桥看见他私自闯进去生气。可他蹲在那瞌睡了两回,一直等到下半夜谢桥也没回来。
他联系不到谢桥了,电话不接,微信不回,应该都被拉黑了,他等在门口蹲了两天,谢桥没会来,反而被查监控的保安找上来叫走了。实在没办法,厚着脸皮上去银行问了,结果人家告诉他,谢桥出差了。
“去哪出差了?”
“俄罗斯。”
俄罗斯?
这个秋天确实是个多事之“秋”,纪真宜脚步沉重地走出银行不久就接到了莫海华的电话。
祝琇莹这些天消瘦乏力,还发低烧,莫海华以为是水土不服,去出差地的医院看病发现腋窝淋巴结肿大,做了b超和乳腺钼靶,查出是乳腺癌。
纪真宜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整个人差点栽下去,眼前发黑,耳道轰鸣,世界都在他脑子里完蛋了。他想,难得扫把星难道成天就盯着他一个人吗,倒霉怎么一层一层全套在他身上?
好在莫海华紧接着说只是早期,不过这个医院医疗条件不太好,问他能不能联系到上级医院转院,毕竟他工作的城市比家乡那边医疗资源要更好一些,也更近一些。
转院如果医生不能给病人联系上级医院的话,就得自己联系。纪真宜满城跑了两天,好点的医院都说没床位,他心里特别虚,总觉得早期到晚期也就那么几天的事,焦头烂额,有种求路无门的无力感。
他去医院采访过医生,现在还加着微信,可人家是个妇产科主任,这可怎么开口。又问了交好的同事上司,大家都挺愿意帮忙,一直帮着联系医院,只是腾床位似乎都挺麻烦的,最近的也要他等两周。
纪真宜联系不到周琤玉很多天了,周琤玉自从话剧那天见过后就跟人间蒸发了一样,再也不见人了,要不然找他的话,肯定会有点路子的。
他这边正心灰意冷,想着明天要还是没有的话,就休假回去陪他妈看见好了,拖下去他心里愈发没底,无力透了。
结果医院主动联系他说,有床位了。
他历经大悲大喜,简直劫后余生。祝琇莹特别悲观,觉得自己已经半只脚踏进坟墓了,郁郁寡欢的,怎么也想不通自己怎么突然就从乳腺增生到乳腺癌了。
莫海华说之前是庸医误诊,好在还算发现及时,以后我再也不气你了。
纪真宜说妈你别告诉我的存折密码了,早期不是什么大病,百分之九十都能治好,你起码活到八十八,我从没想过自己会没有妈妈。
纪真宜这几天奔波在电视台,医院,偶尔回一趟瘦猴的公寓。瘦猴回来了,还成天帮纪真宜他妈熬汤,电视台的同事来探病,带着果篮和花,都说你妈长得真漂亮。
可能这几天实在太过精神丧靡,他坐公交车还被一老太太搭讪了,老太太围着他神神叨叨,拽着他衣服问他要不要加入法轮功,还强行给他取了个法号叫戒色。
纪真宜赶紧下车了,生怕老太太在他面前自焚似的,下了车就报警,说有猖狂的邪教分子对他意图不轨,也不知道警察叔叔有没有空理会。
这段时间忙得无暇联系谢桥,偶尔想到都要难受。
好在祝琇莹的穿刺活检很成功,切割手术的时间也定下来了,和病友交流时人家说祝琇莹的医生是个非常好的专家,手术安排得满满当当,怎么来给他做这种小手术。
纪真宜也觉得这种馅饼掉不到自己头上,他问了所有人都无果,很异想天开地,抱着十分渺茫的妄想给谢桥打了电话,竟然通了。
十分卡卡顿顿地开门见山,“……那个,谢总,我妈,生病,你,是不是……帮忙了?”
喜欢本文可以上原创网支持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