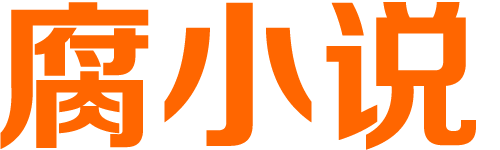吞雨(57)
谢桥好慷慨,“是吗?那我给你减一块吧。嫌贵?”
“没有,挺好。”
谢桥走了。
纪真宜端着碗囫囵几口喝完粥,起身收拾碗碟,从厨房出来,看见刚才谢桥椅子上放着个黑色皮夹,他刚拿起来,正想要不要追出去。
谢桥就去而复返了,“你拿我钱包干什么?”
纪真宜被他用那种冰冷的眼神扫视着,活像捧了个烫手山芋,“我、我没想拿你的钱,我就是正好看见了。”
谢桥只说,“还给我。”
纪真宜递还给他,硬着头皮为自己辩解,“谢桥,我真不至于。”
谢桥接到皮夹就打开了看了一眼,又连忙合上,掀起眼帘觑着他,“你没打开吧?”
纪真宜摇头,他再吊儿郎当也是个有分寸的人,他从来不乱翻人家东西。
谢桥转身就走,“那就好。”
纪真宜站在那,有一点点委屈,他发誓只有一点点,但是还是难受。
他想,我这人再怎么不行,也不至于拿人家的钱吧。
他去电视台,在机房装模作样地剪片子,脑子里走马灯似的一团乱麻。
有人拉开旁边机位的椅子坐下来,纪真宜没察觉,直到女孩子气冲冲地把新买的流浪包甩到他面前,“纪真宜!我要死了!”
纪真宜吓一跳,转头看见丁纷纷水红的眼睛,其他栏目的人看了过来,他连忙把她牵到外面休息室去,“怎么了纷纷?”
丁纷纷是个甜美挂的女孩,家境富裕,“真是没一个能从男朋友手机里活着出来,恶心死了!我还特意跑回来跟他过七夕,你知道吗?他昨天给我转了1314块钱,我给他转了5200,结果这穷逼从我那5200里转了520给一个大三的小女孩。”
她又要气哭了,“我看那女孩还发什么‘爸爸来给我喂糖了’,这女孩说是他包的,还不如说我包的呢,他算老几,中间商给我赚差价!叫谁爸爸?来叫老娘我!”
纪真宜都给她说乐了,丁纷纷下午要上镜,擦了眼泪补妆,跟纪真宜说那穷逼会再来缠她,叫他假扮她男朋友去羞辱一番。
纪真宜说好。
周一例行要开会,会上严正说明了新闻里用的国家地图绝对不能出岔子,要是缺哪块少哪块,大家一块滚蛋。
罗总可能事后想起昨晚说的是南关口,会上明里暗里夸纪真宜挽回,“……大家还是要努力为栏目争荣誉,像我们纪老师去年就得了台里的爱心记者称号。采访低保户廖淑贞老人,年轻时对国家有贡献,但晚年生活困苦,纪老师慷慨解囊当场捐助五千元嘛!”
电视台大家都互称老师。
同事起哄,掌声雷动,纪真宜装出一副荣誉加身的样子,“过奖过奖”地站起来。
罗总接着说,“台里也很为这种精神感动,特地奖励了我们纪老师250元。”
顿时切声四起,好一个二百五。
纪真宜又坐下了。
开完会,大家三三两两都走了,纪真宜去八楼机房接着剪片子,正好罗总来逛机房,“怎么还在?”
纪真宜存好档,“正要走呢。”
罗总叫他留一下,两人去机房外面的环形窗抽着烟聊天,“你们应该早听到风声了,你们二组申圆喆要调去演播厅,空下来这个缺,我和毛总的意思大致相同,不是你就是田心。”
“哦,就他吧,我当个副的就行。”
罗总说,“哪有副的?”
“没关系,名义上做个副的就行。”他笑起来,“您看我这人吊儿郎当的不靠谱,不还把南关口听成西关口了吗?再说他比我需要,也比我合适,我无官一身轻,当不了大任。”
罗总说,“我看不是。”
“罗总那您真是看走眼了。”
“嘿!”罗总作势要发火。
纪真宜麻溜往电梯跑,嬉皮笑脸,“谢罗总栽培,发工资请您吃饭。”
话出口又愁得直拍脑门,哪还请得起饭啊,撇去寄给他妈的那一半钱,等他付完谢桥那9999块钱房租,估计吃根贵点的冰棍之前都要给自己打个气,“加油纪真宜,你值得!”
第四十四章 等啊等啊等啊
其实说来纪真宜和田心收入都不低,虽然自嘲一句新闻民工,可电视台记者大小是个招牌,总有外快赚,台里外包的活分配到他们也有提成。田心还无心插柳柳成荫,做成了个挺有名气的自媒体,每天忙得连轴转,但收入非常可观,可惜家里背债。
纪真宜能画能拍,私活公活都接,挣得虽多,但买起镜头来也花钱如流水。
他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打开了公寓的门,瘦猴还在邻市出差,微信上和他说了一声,收拾好行李,打个车去谢桥那了。
半路叫师傅停一下,去买了个蛋糕。
进小区时正好遇上谢桥下班回来。
他看谢桥又穿着西服,觉得银行工作也不容易,大夏天都得裹两层,虽说工作场合大多在室内,可也总有外出的时候。又一想自己拍新闻成天在外面跑,不由有种农夫操心皇帝起夜撒尿穿鞋会麻烦的杞人忧天。
谢桥顺手帮他提个箱子,开了门进去,“等会儿把你指纹存上。”
纪真宜把蛋糕拎起来,“谢总,切个蛋糕吃吧。”
谢桥有些不解地看他,好像在思量今天是什么日子。
纪真宜笑起来,“恭喜我搬家。”
“我吃过饭了。”
“再吃一点点吧,买都买了,当饭后甜点好了,不会很腻的。”
谢桥被他缠着,勉为其难地坐下了,拿小圆勺斯文地吃进嘴里。
纪真宜坐对面看着他,年少的记忆浮光掠影般泛上心头,谢桥吃红豆米糕,吃栗子,吃小曲奇,笑着对他说“好吃”的模样,好像在近在昨日。
谢桥突然抬头,纪真宜心都横跳了一拍,垂着眼心虚掩饰。
“早上,我没怀疑你要拿我的钱。”
纪真宜有些错愕,好一会儿才想起来,“哦,我知道啊,当时就是刚醒脑子乱,想茬了。你要真怀疑我拿你钱,也不会还把房间租给我。”纪真宜笑吟吟地看着他,深深的,简直要把他融在眼底,“是我错了,误会你怀疑我,对不起啦谢总。”
纪真宜晚上一个人在卧室收拾行李,蹲在地上把东西一件件拿出来,多是衣物和摄影器材。一直到箱底收着的贝壳和红绳,旁边还有一罐子贝壳。
红绳很老旧了,上面挂着的银铃铛都氧化发黑了。他以前整天戴着它,心都像吊着块石头一样沉沉坠着,多看一眼,五脏六腑都要搐疼。
红绳断掉的时候,他清楚地知道,不是韩放筝放过他了,是他放过自己了。
鲁迅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句话后来又传演成悲剧就是将美好的东西毁灭了给人看。
他想,不管怎么说,韩放筝死了都是个悲剧。不是因为他才悲剧,是韩放筝本身就是有价值而又美好的,撇开纪真宜不谈,这样一条恣意鲜活生命的逝去本就让太多人无法释怀。
纪真宜未必是这些人中最重要的,但他一定是最自我折磨的。他难过的时候,好像一条鱼,身上每一块鳞片都在切割他的皮肤,看不见的鲜血淋漓。
人的情绪是很驳杂的,而且矛盾。
其他人也这样,希望他为韩放筝的逝去难过,却又不希望他长久的耿耿于怀,他们希望他有度的悲伤,从哀痛欲绝到释怀坦然必须是个所有人都能看到的递进的过程。
该难过的时候他不能走出阴影,要不然是畜生,该重获新生的时候还形单影只,又劝他忘了吧。
到底是时间在做刻度。
他不想再困囿不前,他不想永远在背负着回忆那片雨后的阴霾下踽踽而行,他想被牵着跑进粲然欢欣的春光里。
谢桥回来了,这个不一样的谢桥,他也喜欢。
纪真宜想,喜欢就喜欢,多简单,喜欢就追啊。
经年未见又怎样?
只当两个全新的人,溺进了一场全新的爱情。
喜欢本文可以上原创网支持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