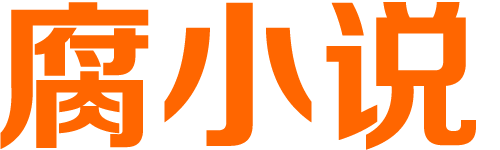吞雨(45)
纪真宜到最后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回家的,他只记得他抱着他妈哭了好久好久,他自己要被自己的眼泪淹死了,整个胸膛都是破碎的全是啸音。
他关了门躲进房间里,祝琇莹在外面哭着不停敲门。他只好说,妈你让我待一会儿,我一下下就好了,我求求你让我待一会儿吧,我不做傻事……
纪真宜哭得脑子发晕,脑仁嗡嗡阵阵,他抱着腿坐在床上,从头到尾捋顺这件事。
这所有的乱七八糟的事情里,谢桥是可以摘出来的。
谢桥多可怜,他从头到尾都无辜。
纪真宜发现自己做错了,错得离谱。校考回来的那天晚上他就该明白的告诉谢桥,或许更早,谢桥开始对他笑,对他撒娇,他就该叫停打止。
这样来来回回,既躲又藏,给一颗甜枣又给一场空欢喜,钝刀割肉最可恨。
他和谢桥开始的时候,他没想过谢桥会喜欢上他,更没想过自己会舍不得。那么多潜移默化,抽丝剥茧,情难自禁,他和谢桥的关系或者说他对谢桥的感情都太复杂了,变得难以言明。
他总想找个最无害的理由,其实最好不过当断则断。
他开门出去的时候,谢桥就在守他门外,正因为他在,祝琇莹才敢放心出去。
纪真宜嘴唇枯白,像久置的蜡像一样虚弱,朝他扯开一个苍白的笑,“小桥。”
谢桥捞过他,飞快进了浴室。
纪真宜撑在盥洗台上,被操得两腿战战不止,脚尖都立了起来。胯骨撞在臀上的声音既重且闷,谢桥从身后掐住他下颌逼他泪眼地看着镜子,也不说话,只沉默地边操着他边让他直视自己。
性器是热烫的,仿佛刑具残忍而机械地开扩填充着肉体,两个人都浑身冰冷,无声嘶吼着的绝望。
谢桥咬着他肩膀,深深射进他身体里,纪真宜两腿之间一塌糊涂,他若无其事把裤子提起来,两条细白的腿还在打摆子。
“最后一次,再也不要这样了。”
谢桥站在他身后,“你一点也不喜欢我吗?”
纪真宜狠狠闭了一下眼睛,没有回头,“你第一次跟我说喜欢的时候,我就告诉你了,我不喜欢你,我和你没有可能。”
“你为什么还对我那么好?”
“因为我坏啊,我有病,我犯贱好不好?”
“你既然不喜欢我,为什么要和我……”
为什么对我好?为什么和我做爱?为什么给我无数个我们一定会有未来的可能?
纪真宜转过来,“因为你长得太好看了,性格又很可爱,谁和你住在一起不会想和你做爱呢?”他说得那么理所当然,好像全是谢桥的错,“而且,第一次硬闯的不是你吗?我又没叫你喜欢上我。”
谢桥第一次感受到这种切实的欺负,“你讲不讲理?”
纪真宜看着他,脸上是谢桥常能从他脸上看到的那种笑,哀悯温柔,“不讲啊。”
第三十五章 (上)我第一次喜欢一个人
谢桥孤直地站着,眼梢洇红,薄唇紧抿,一下就哭了。
他白得欺霜胜雪是玉做的人,眼泪一落像晶润的滚珠。
这两滴泪落下来,把纪真宜心都砸成馅了,方才的伪装全作了废,“小桥对不起,对不起,不要哭小桥。”
他方寸大乱,觉得自己罪大恶极。又错了,他又错了,谢桥被他欺负哭了,他到底该怎么办?
他高考的后一天才满十九岁,他并不很聪明,他做不到面面俱到,他没厉害到能让所有人都称心如意,他不能保证自己的每个决定都不出错。
他也会自私,很自私,他会想有一个让他暂时栖存喘息的港湾。
每晚灯熄下来,夜晚空空寂寂,他躺在床上,胸口都压着一座大山。一到下雨,他就开始感同身受韩放筝死前那种要将人吞溺的悲伤和冰冷的绝望,他太冷了,太害怕了,他渴望一些让他偶尔忘记痛苦的热火和一个足够包裹他的怀抱。
性爱多好,身体燃烧,思绪沸腾,他不觉得有什么,你情我愿,谁也没逼谁。
他对谢桥好,一方面是他本性就这样,他下意识不想让身边的人难过,另一方面,谢桥实在过于可爱,尤其本性与外表的反差。
他从小就讨厌故事里被偏爱的那个人,谢桥从哪看都是那个人,唯一的烦恼不过就是担心母亲有了新家庭不再那么爱他,可连纪真宜也要偏爱他,他连这点烦恼也不想让谢桥有。
偏偏谢桥喜欢上他了。
“小桥别喜欢我了,你看我这个人,一无是处,哪里值得你喜欢呢?小桥的喜欢那么珍贵,不能随便给人啊,我配不上小桥的喜欢的。”
谢桥用一双浸着泉的殷润的黑眸注视着他,“你又哄我。”
“才没有哄你,是真的。以后跟你在一起的人,一定又聪明又好看,纪真宜是什么呀,跟人家相提并论都高攀了。”
才不是,你明明是最好最酷的纪真宜。
“你把我当性启蒙好了,把我当个飞机杯也行,我根本配不上你的喜欢。”
“你凭什么这么说自己?”谢桥看着他,深深地,破碎地看着,“我第一次喜欢一个人。”
纪真宜的心都跟他一块碎了,他对谢桥的感情太复杂了。他简直把谢桥当自己养的小宝宝,又乖又可爱,一笑起来,整个世界都成了糖做的。
“对不起,小桥,我太坏了。”
门口响起窸窸窣窣的动静,大概是祝琇莹回来了,谢桥偏头过去,不留痕迹地错身出去了。
纪真宜无力再挪步,他整个人都成了灰色的,死气沉沉。
谢桥坐在桌前,他无意识地摩挲着那个草莓玻璃杯,空落落的。突然响起叩门声,纪真宜在说话,“小桥,吃饭了。”
谢桥浑身一耸,腾地起来了,杯子从桌沿降下去,谢桥眼睁睁看着,砰——的一声。
碎掉了,画着Q版谢桥的,喝白水都是甜的杯子,碎掉了。
天阴了一整天,雨是在晚上来的,雷声闷重,雨帘长长不断。
谢桥开了盏台灯,专注地看着眼前碎开的玻璃片,来回拼了几次,都没成功。
他突然有一种无力感,就像他当时喜欢上纪真宜一样,根本不能由自己做主。
他明知纪真宜虚弱,颓靡,花言巧语,是蝴蝶的鳞粉,既毒又呛人,可偏偏还想伸手握住。
他浑浑噩噩地打开冰箱,当然是没有酒的,他也没想要喝酒,酒有什么好,多难喝。他把冰箱里剩的六瓶旺仔和三瓶AD钙全拿出来,搂在怀里回房间了。
上次,他在圣诞夜等了纪真宜整晚等来一句“关你什么事”的那次,也半夜起来喝了七罐旺仔,喝到最后他都觉得自己醉了,可能是醉奶吧。
又或许难过和牛奶能酿酒。
他单手拧开拉环,仰起头一口喝到底,如此往复了五次,喝完的牛奶罐颓废地东倒西歪。
谢桥倒在床上,觉得脸上有点发热了,要开始醉了吗?
他想或许真的该把纪真宜的腿打断,然后在他身边筑起高高的篱笆,把他藏起来,所有人都找不到他。把纪真宜脑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人和事全部洗掉,洗得干干净净,那纪真宜就不会难过了,是一个崭新的纪真宜了。
那纪真宜还是纪真宜吗?
这不就是忒休斯之船?替换了部件的船还是原来的船吗?
雨悄悄停了,夜阑人静,谢桥轻轻打了个充满哲思和寂寥的奶嗝。
他又想,不行的,小美人鱼困在篱笆里会死的,鳞会脱落,血管会干涸。
他坐起来,把吸管插进AD钙里,喝了两瓶,觉得不行,有点酸,真奇怪,为什么纪真宜给他的AD钙是甜的?
纪真宜的AD钙是盗版的吗?
真坏,什么都骗我,连给我的奶都是假的!
他坐在床沿,怔怔地开始胡思乱想,窗口溜进来的斑斑月光折在桌上的天文钟上,快要五点了。又过了会儿,窗外成了雾沉沉的蓝色,天明得越来越早,又要跨进一个新的夏天了。
上次他一整夜没睡,七罐旺仔牛奶促使他做了个决定——他再也不理纪真宜了,当然失败了。
喜欢本文可以上原创网支持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