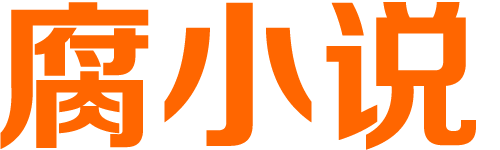寄生+寄生Ⅱ(32)
“真不觉得疼?”他沉着脸看我。
我指了指脑袋:“你是指这里的神经反应?当然疼。但并非无法忍受。”
对面漆黑的眼睛里有种一闪而逝的情绪,由于太过细微,我辨认不出来。他接着追问:“那么让你无法忍受的是什么?”
我认真地想了想,答道:“失去自我,或自由。”
他向后靠在沙发背上,嘴角扯出一个不知是嘲弄还是自嘲的弧度:“如果是这两样,你完全不必担心,我不知道这世上还有什么人能强迫你。”
“就目前遇到的而言,的确没有。”
何远飞慢慢仰起脸,盯着白色的机舱顶,仿佛陷入深思。许久后,他恨恨地嘀咕了一句:“有时我真想掐死你算了……”
这句很可能是实话,但我猜它永远没有实现的那一天。
倒不是因为相信这个人类男人对我的“爱”——就算这种感情当真存在,对它的稳定性与时效性我也报以彻底的怀疑。这玩意儿就像电脑病毒,平时看着是个普通文件,一旦发作变异就会具备可怕的杀伤力,所幸的是,只对人类有效。
实际上,是因为我知道这个星球几乎没什么东西可以威胁到我的生命安全,除了强雷电与更高文明的侵略性物种——对前者我比从前更加谨慎,一般会提前躲避,而后者,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在地球上遇见过。
至于人类,比如我面前的这个男人,即使在他的同类中算是比较强悍的,我也从没把他的威胁放在眼里。有时我甚至会百无聊赖地预想,当某一天这个男人的大脑中名为“爱”其实不过是多巴胺分泌的化学反应过了保质期,他或许会再次把枪口顶在我的太阳穴上。如果我们之间维持的和平友好的局面分崩离析,我是不是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把他的强健身体据为己有?
对面闭目养神的男人忽然睁开眼直视我,“你在打什么坏主意?”他语带警惕地问。
我的本体蓬出一簇微小的神经电流火花来表达对他直觉准确度的惊讶,而反映到宿主的身体上时,只是一个“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的无辜表情。
“你在眼神里冷笑,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他倨傲地抬了抬下颌,架起长腿,一拍身旁的坐垫:“坐过来。”他命令道。
既然产生怀疑,为什么还要叫我近身,这个男人到底在想什么?如果是因为无聊拿我来消遣,我不介意跟他虚以委蛇一番。
按他的要求坐下,我摆出公司小职员通用的嘴脸:“老板,请问有什么吩咐?”
“吩咐?有——”何远飞侧过脸,纯黑的眼睛戏谑似的斜着我,“不准用牙咬。”紧接着,他用右手抓住我的后颈,吻了上来。
他的唇舌带着不容反抗的掠夺意味,而我对这突如其来的激情有些意外。
虽然知道人类是可以随时随地发情的动物,但我并未发现之前短暂的对话中有什么刺激到他性兴奋神经的地方。
或许他是在以这种方式确立我们之间的主导地位,就像雄性野兽在地盘上四处撒尿散播自己的气味一样?
如果是这样,我不能让他以为我是处于下风的那一方。
我不知道回吻是不是应该像他那样又舔又吸,但作为一个出色的模仿者,我敢肯定在强度与持久力方面比他有增无减。
被我压倒在沙发上时,他发出了一声诧异的鼻音,试图把位置翻转过来。
我坚决不能够让他得逞。据某个人类心理学家说,身体姿势也是体现支配者与被支配者的途径之一。
经过一番漫长的较量,我发现宿主的大脑出现缺氧的征兆,不得不松开来换气。
何远飞的胸口在急促的呼吸中起伏,手掌沿着我的脊背一路滑向腰下,低沉沙哑地轻笑道:“宝贝儿,你今天热情得出人意料……想不想试试在一万英尺的高空做爱?”
“不想。”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打算起身回到原来的座位上去。
他用双臂搂紧我的腰身,不死心地继续说服:“你不能总这么拒绝我,亲爱的,做爱是情人之间的乐趣和义务。”
“义务?我不知道还有这种说法。”
“你挑起了我的性致,就有责任平息它。再说,我们曾经做过,你也享受到了高潮不是吗?其实这事并没你想象中那么麻烦,只要点个头,其他都交给我就好……”
就算他舌灿莲花,我仍然对与人类性交这种浪费时间、毫无意义的行为兴趣缺缺。
而且对他说的“曾经做过”我必须申明一下:达到性高潮的是宿主的身体,这是神经刺激下的本能反应,与我无关。我的本体并不具备人类那样的生殖系统——即使有,也不支持异种性交。
另外,还有一点需要纠正:我们不是情人,只是同居者。
我看了看手表,对他说:“飞机十分钟后降落,或者你想让人见识一下老板被手下压在沙发上的情景?”
何远飞失望地叹口气,悻悻然放开了我,点了根烟来中和浑身欲求不满的气息。
回到洛杉矶的别墅时,是上午十点左右,还赶得及吃一顿不算早的早餐。
我填饱宿主的肚子,洗了个澡,从浴室出来直接爬上床,准备补回一夜未眠的觉。
刚躺下五分钟,何远飞径自打开房门走进来,脱了浴袍钻入被窝,从背后抱住我,粗壮的胳膊圈在我腰上。“空调开太冷了。”他拉高棉被,小声地抱怨。
从对方皮肤传来的体温令我觉得有点不舒服,为什么他不是冷血动物?我用手肘顶了顶他,“怕冷回自己房间睡。”
他没有回答,一条腿跨过来,手上抱得更紧了,下巴搁在我的颈窝,细暖的吹息拂在脸颊,如同宣告占有权似的把我圈在怀里。
不够凉快,但很安静。
于是我睡着了。
直到被一阵电话铃声惊醒。
即使进入熟睡状态,我本体某一部分神经末梢仍然保持着警觉,几乎是铃声响起的瞬间便激活起来。与之相比,这个人类宿主的身体反应就迟钝多了,我花了好几秒的时间,才指挥着它从疲倦中彻底清醒,起身准备去接听电话。
一只手握住我的肩膀按下去,回头一看,何远飞醒了,表情还有些惺忪,带着点鼻音说:“我去接,你继续睡。”
他披上睡袍走出卧室。虽然宿主的身体机能还未完全恢复,但我觉得接着将要发生的事情不容错过——虽然还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事。我从不抗拒这种用人类的话说叫“预兆”、“第六感”的本能,于是也披了件睡袍跟上去。
电话是门卫室打过来的,说是有个寄给“何总裁”的重要包裹需要签收。
很快,经过扫描确认无危险品的包裹被送进来,轻飘飘的没什么分量,上面没有填写发件人的相关信息。何远飞拎起包裹掂了掂,兴趣缺缺地丢到一旁的茶几上,转身对我说:“怎么起来了,也不多睡会儿……还是说,先来点睡前运动?”
我没有理会他拙劣的语言性骚扰(尽管他本人称之为调情),走过去拆开了那个包装得相当严实的包裹。
里面只有一张光盘。
“……你邮购的新GV?”我朝何远飞挑了挑眉。
他厚颜无耻地回答:“等你把电脑里的那些看完,我再给你拿新的。”
“用不着,我已经把它们当垃圾文件删除了。”明知没什么效果,但我想还是必须再抹杀一次他的侥幸心理,“就算你把万维网上所有的GV都塞进我的笔记本里,我也不会对生殖器和肠道的活塞运动感兴趣——和口腔也一样。”
喜欢本文可以上原创网支持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