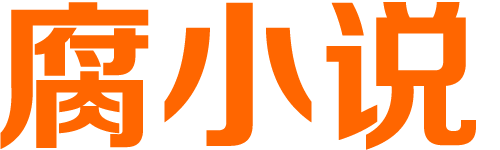一银币一磅的恶魔(45)
最高的那个修士从卧室里退了出来,用左手跟其他三人打了个手势。“敌袭,恶魔”,是这个意思。他微微佝偻着身体,脸上没什么表情,右手以不自然的角度垂挂着,显然已经断了。他又打了一个寻求治疗的手势,阴沟鼻修士上前治疗这面无表情的伤员,先处理腹部,再处理胳膊。
要做完这个,他们才会去处理房间里的“那个”。
你看不见卧室里面的光景,你不必去看也能知道个大概。从他们带兜帽的法袍到看似平凡无奇的木鞋,每一个地方都纹着最高等级、使用最珍贵材料的驱邪祷言,甚至远胜过要正面与恶魔交战的十字军——黄袍修士在教廷中地位不高,他们的姓名与性命都无人在意,然而当他们身负迎回圣子的职责,他们就成了某种神圣的象征。
教廷分工明确,有专人处理尸体,他们只需要带你走。如今他们还停留在那里,雷米尔必定还活着,只是绝对不太好。倘若他安然无恙,他不可能对门口大喇喇处理伤口的两个修士坐视不管。你真的不知道吗?雷米尔不会不战而逃。
你听见低语声,来自你的身后与身前,只须听见前几个音节,你就能说出这祷言来自哪一篇哪一节,完成后会如何起效。他们不如你,不会无声祷言的本事,但四个人就是一组,像四个部件构成一只绞肉机,那个未完成的新式祷言还不足以抵挡。他们没问房间里为什么有个混血恶魔,也无意向你寻求解释。工蜂们无权审判你,他们只知道,恶魔杀无赦。
“请停下。”你上前两步,竭力保持着语调平稳,“我在它身上有重要发现,圣所会处理它,你们没有资格擅自破坏。”
他们停了下来,看着你。
上前几步以后,你已经能看到门内。你看见雷米尔在地上挣扎,像被无形的重物压着,他胳膊上有很大的伤口,没有渗血,仿佛被烙铁压过。你不敢仔细看他,只抬头看着你的同事们,汗水渗透了你的里衣,而你的面容平静无波,跟他们一样。
我们是相同的,都是天主的子民,你在心中重复着,像误入死灵国的人祈祷自己的皮肤足够冰凉。我们是相同的,我全无私心,我没有想保护他,我没有撒谎,我没有为了半血的恶魔、为了我禁忌的恋人欺骗天主的牧羊人——你拼命地自我催眠,仿佛这样就能说服自己与周围的所有人。
你知道教廷分工明确,各个关节各自独立,并不共享信息,因此你可以编出听起来像模像样的理由。有一半可能他们会听从,只是也非常可能直接把雷米尔跟你一起带回去,那对雷米尔来说没准比死还糟糕。可是现下你顾不得想,你的每一条神经都在尖叫,你的各种思绪告诉运转不断碰撞,只有一个念头凌驾于这一团乱麻之上:雷米尔得活下去。
他们看了你一秒,三个人转头看向拿着罗盘的人。拿罗盘的修士犹豫片刻,打了个手势。
你的心下坠。
迎回圣子的搜寻队没有知道圣子要做什么的权限,同样也没有配合圣子做什么的职责。他们的任务只是带你回去,另外,所有圣职者都知道,恶魔杀无赦。
这死板的教条最终得出了死板的结果,他们要杀了他。
这短暂的瞬间被拉得很长,你的脑袋轰隆作响。别这样,这不是真的,还没有坏到这个地步,你徒劳地祈祷,乞求着天降转机。主啊,请帮帮我!你在心中哀求。你这一生的九成九时间都是乖顺虔诚的羔羊,你听从主的意志,难道不是神让你离开了那里,让你遇到了雷米尔吗?为何神又要将你带回,又要将他带走?你会回去,你会去到主身边,你愿意用余生与此后的永恒侍奉神明,你不会再渴望那些不属于你也不该渴望的东西了,但是只有雷米尔,雷米尔得活着,哪怕此后你们再不相见。你知道他比起天堂更爱人间,倘若你是家鸽,他便是野鸽,他在鸽舍里活不下去,无论那笼子有多富丽堂皇。你只能祈祷,祈祷着神的怜悯与恩典……不然还能怎么做呢?你不能。主啊,主啊,不要抛弃我!
祷言响了起来,没有任何转机从天而降。
你终于低下头去看雷米尔,不再管是否会暴露。雷米尔不再挣扎了,他正看着你。
你曾属于他们,你清楚什么手势代表着什么意思。雷米尔不了解他们,但他了解你,当他捕捉到你那一瞬间微变的神情,他就知道了自己的判决。祷言已经响起,不久就会完成,他会被“净化”,那灼烧之痛想必已经覆盖到了雷米尔身上,可他只是看着你,镇定非凡。你从中看出期待,并非你乞求天主垂怜的那种期待,而是某种孤注一掷的催促。
仿佛此前无数次,他驻足等待,回头看你。
于是你明白意外并非意外,他故意在门里撞出了声响。雷米尔不会不战而逃,更不会坐视他们把你带走。承认吧,你知道的。
神明悄然无声。
这些日子来反复推敲钻研的反向祷言在你脑中堆积,你梳理它们,如同谙熟的纺织工抽丝剥茧。你的心中再无杂念,只有敌人的站位,战场环境与你的武器。你朗声念诵出逆性的词汇,像过去念诵驱邪咒文一样坚定不移。你根本不知道它能否奏效,在旁观结果之前,你猛地向后冲去,撞倒了手持罗盘的修士。
他是领头人,传讯道具一定在他身上。他伸手护着罗盘,于是你得以将手伸进他的暗袋之中,摔烂信号弹,撕碎还未起飞的圣鸽。你离开近六年,六年对于古老的教廷而言只是一个眨眼,你所知的那一套一点都没有改变。你知道怎么拆除那些防护,正如他们知道如何拆开你的家门。
那结实的锁链缺了一角,雷米尔暴起挣脱,快如闪电。你持续不断的咒文与前些时日以来刻印在雷米尔身上的符文共鸣,成为他的铠甲,成为他对抗神圣的剑与盾。你听见背后激烈的打斗声,这些声音被各式祷言护在房间以内,安睡的街道不会知道神父的房子里正在发生什么。
你没有回头,你正缠住面前的敌人。这等修士并非文职人员,他们是教廷的军队,动起手来毫无慈悲。后方的另一位修士大概踢断了你的一两根肋骨,但你紧抓不放,将两个人都留在你这里。你接受过最好的训练,你八岁就上了战场,在战场上待了十二年;你始终保持着锻炼,清楚自己的战斗力,也了解面前的敌人。你被当成最上乘的牺牲,当成需要层层软布包裹的珠宝,但很多人忘了珍贵的宝石往往无比坚硬。
那罗盘终于砸落到地上,摔碎了一角,血腥味弥漫开来。你依稀看见里面一片鲜红,只是一接触空气就变了色,散发出一股腐肉的气味。拿罗盘的修士被你砸昏在了桌角边,另一个则在之前被雷米尔拉进了他的战团。你回头,只见雷米尔正与两名修士搏斗,还有一人被扔了出来,在墙上撞得头破血流。你回头的时候,那个人正爬起来,对着雷米尔开枪。一枪落空了,另一枪擦过雷米尔的肩膀,那里展开一蓬血花。
他们想伤害他,他们想杀了他,在你眼皮子底下。
他们怎么敢?
那一蓬红色不曾离开,它烧灼着你的眼睛,让你的视野也一片猩红。你忏悔,服从,恳求怜悯,你后退,直到退无可退。被踩到最低点的弹簧终于反弹,在恐慌和悲伤之外,怒火从你的骨骼中爆发出来,你的血液在燃烧。
你炮弹般撞上开枪的人,把那个人摁倒在地,他的枪飞出去,没飞太远。你掐着他的脖子,余光看见他的手还在摸索着去够枪。桌子已经被打翻,上面的东西洒得满地都是,那支本打算用来给雷米尔留信的钢笔静静躺在枪边上,笔帽不见踪影,笔尖泛着金属锋利的光。
谁都别想在你面前伤害雷米尔,谁都别想。
你拿起了那支钢笔,高举,重重向下刺。笔尖毕竟不是刀尖,拿来当武器够呛,但要是对着眼睛,那就另当别论。你下刺,拔出来,再度下刺,又狠又准,每一下的落点都在同一个位置。那修士终于惨叫起来,墨水和鲜血在他脸上纵横交错。瞧,他也只是血肉之躯罢了。
上一篇:人类变性第71年[星际]
下一篇:门后高能[无限]
喜欢本文可以上原创网支持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