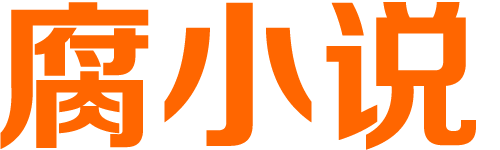有钱(75)
接着,沈白打开门锁,把景霖打横抱起来,大步向外走,温声道:“夫人把脸藏起来。”
景霖偏头,把脸埋进沈白衬衫。
衬衫料子凉滑,去了外套愈发显身材,那蓬勃的胸肌、坚实的手臂、宽阔的肩、悍利的腰……在眼下正式的、讲求礼节的、名流汇集的场合中,有种几乎不合时宜的狂野性感。
沈白并不打算引人注目,也不在乎名媛们灼热得能洞穿铁板的视线,专拣人少的地方,横抱着景霖快步走出会场。
……
车子滑行进车库大门。
引擎熄火,司机下车绕到后面开门,沈白摆摆手,示意他离开。
车库里只剩他们两人。
“到家了。”沈白拨弄景霖耳垂,“睡着了?”
景霖抬抬下巴,眸光清明,含混道:“……没。”
从离开会场开始,沈白就发现景霖模样渐渐清醒,或许是被外面的凉风吹醒了酒。这一路上,景霖神色愈清,埋在沈白胸口的面颊就越臊得烫人,大约是想起之前的黏人醉态。
车内气氛有一瞬间紧绷。
就在沈白以为景霖即将恼羞成怒大闹一场时,景霖却僵硬地,往沈白怀里拱了拱。
两人贴得那么紧,沈白能清晰地感觉到景霖的心跳,怦怦、怦怦,比之前还快上许多。
他垂眸,眼珠带着一种病态的漆黑,不动声色地将景霖端详着。
景霖眼珠乱转,贼兮兮的,自以为玩心眼儿玩得毫无破绽。
沈白不戳穿,只问:“感觉好点儿了吗?”
景霖涩声答:“没好。”顿了顿,此地无银道:“好像还……糊涂着。”
沈白抿了抿唇,止住笑:“你再不好……我要乘人之危了。”
景霖别扭地模仿之前的醉态,借酒装软:“嗯……乘、乘你的。”
沈白喉结微微滑动,顺势将他按倒在柔软的后排座椅上,俯身亲昵片刻,忽然慢条斯理地抛出一句:“今天我让你来,你不来,非得偷偷跟踪我……什么意思?”
怀疑错了人,景霖自知理亏,哼唧装醉:“嗯?嗯……”
“想看我在外面老不老实?”沈白直起身,扯了领带啪地甩开,又拉开几枚扣子,虚压回去,咧嘴一笑,眼珠黑得骇人,“我最老实了,我这辈子……”
他贴上景霖耳朵,玩笑的口吻道:“还是个处呢。”
这话说起来有些好笑,景霖却笑不出。
都说小别胜新婚,这样一个人,一别多年,历经死生契阔,却心如磐石,不曾转圜,如此的热烈蓬勃与坚韧不移,令他们两人都像生了寒热病般,亢奋得浑身战栗。
“上辈子也是……”沈白用力吻住他,热烈得像要吞吃什么一样,嗓音病态地颤抖,“我只有你,真的……只有过你……”
……
……
……
第57章 狼爱上羊(十四)
晨光熹微,主卧内氛围暧昧。
空气中浮着一股石楠花开的腥甜味道。
昨夜先是车后排座,随即又是卧室,需索无度……
景霖醒来时,发现自己被沈白按在胸口,一条结实手臂沉沉横在背上,手握着肩头,是一个占有欲强烈的姿势。
昨晚褪下的衣物堆在地板上,景霖支起身,胡乱扯来一件就往身上裹。
他像是余韵未褪,一身皮肉处处透着粉,让晨曦映着,连毛发都细腻得像桃绒,模样馋人。
沈白早已醒来,也或许是压根儿没睡。他摁着景霖折腾了大半宿,眼神却仍荒得骇人。
“脏了,”他无赖地扯景霖袖口,“别穿了。”
景霖负气甩手,显是被弄狠了,奓毛了:“你未免也……”
沈白浅浅咬着嘴唇,含笑问:“未免怎么?”
景霖横他,眼睛又湿又亮,像水中浸的寒星,想起自己前夜的种种表现,身子羞得微微发颤:“未免也……太、太放荡……不知节制!”
沈白倏地柔和下来,轻轻将他望着,抛出一句:“洞房第二天早晨你也是这么说的,神态也像……记得吗?”
景霖眼皮微微一抬,想起来了。
自己当年确实说过差不多的话。
“我对你节制不了,独守空房这么多年,都憋出病了。”沈白半开玩笑地说着,碰瓷儿般攥着景霖腕子不放,温声道,“夫人赔我。”
他观察景霖神色,猜他会如往常一般,先斥他无赖,再别扭同意。
岂料景霖只是僵了僵,极快地瞥他一眼,便嘟哝着问:“……怎么赔。”
“搬进主卧,行吗?”沈白晃他腕子,像小孩儿撒娇,嗓音却低沉温柔,“想抱你睡。”
“嗯,”景霖企图轻描淡写装不在意,奈何脸红得厉害,显然在意极了,“我搬便是。”
“这么乖?”沈白讶然,试体温一样抬手去碰景霖前额,“头脑又清楚些了?有吗?”
景霖略一感受:“清楚着呢。”
这一晚过去,他神智确实像是又清明了些,旧事也差不多都忆起来了。
沈白眨眨眼,考他:“勾三股四弦几?”
“弦五。”景霖蹙眉,“你当我傻么?”
沈白:“你以前说弦七,因为三加四得七。”
景霖:“……”
沈白:“我说弦五,你就打我。”
景霖一怔,听不得脑子糊涂时干下的蠢事,低头匆匆系扣。
可他越不敢想,有些蠢事就越往前边凑:光着屁股一飞冲天、立在路旁看大汽车、抡拐杖追打叶辰、出门跟凡人耍威风却被凡人气得蹲在桥洞里哭、在派出所作威作福……
景霖面红如血,头越埋越深,简直恨不得把脖子撅折脑袋塞腔子里去,慌得把中衣扣子系错了,一错错一排。
沈白端详他,猜出大概,伸手解开他系错的扣,将中衣拉开,眼睛朝里觑着,似责备,却更像揶揄:“糊涂的时候动不动往天上飞,也不管旁边有人没人……”
景霖身子没他那么精悍硬实,是东方式的匀称柔韧,肌肉稍单薄些,但自剑突往上,也有一道胸肌拢出的、浅浅的凹痕,非常漂亮。
沈白盯着那一道,慢声道:“别人也看过,我吃醋了。”
“我……”景霖理亏,嗫嚅着,“都没人……我飞得快。”
这话倒不假,眨眼功夫人就飞没影了,就算有凡人,其实也看不清什么。
沈白嫌他窘得不够似的,又打趣道:“那天你找不着家,去派出所找警察,辰哥说你跟警察要宫女,我当时没问你,你当国师那段时间……老实吗?”
景霖猛地抬头,惶急道:“我只是听她们唱曲儿,连跳舞都不曾看过,你别冤枉人!不信你……你……”
也没个能出土作证的宫人!景霖又气又急,面颊红胀,直想打人。
“信你,不用作证也信。”沈白逗弄够了,帮他系扣,指尖拨拨那复古的白玉扣,忽地道,“今天我陪你做几套衣服?”
景霖穿衣讲究,各朝各代的服饰都有不少,唯独现代风格的衣物一件也没有。
不仅是衣物,除了改良版的马吊——也就是麻将之外,景霖抗拒一切来自新时代的事物。叶辰好说歹说,勉强给他配了手机,他也只懂得玩线上麻将,连打电话发微信都不要学。
脑子不好、懒得学、不喜欢变化……或许都不是真正的原因。
沈白想着想着,无声地叹了口气。
……
这家高定店不起眼,隐蔽在城中一片绿荫深浓的老式洋房区,门脸小,路也难找。它不张扬,亦不屑于张扬,手工费、布料、设计费,皆贵得能把误闯而入的路人血压拉满,因而仅接待老客,像旧日的贵族。
喜欢本文可以上原创网支持作者!